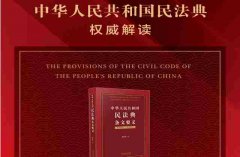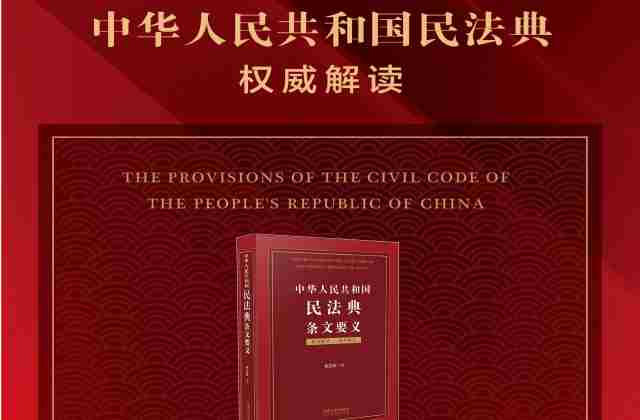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的平等是
宪法的平等原则在民法上的贯彻。我国《宪法》第33条第2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从根本法的角度确定了公民的法律地位平等。平等原则作为《民法典》的基本原则之一被规定在第4条:“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的法律地位一律平等。”
为贯彻作为《民法典》内在价值中的平等原则,在《民法典》总则编民事主体制度中首先规定权利能力的平等,只有承认权利能力的平等,民事主体才能称之为平等主体,不同地域、收入、职业、服务的人在民法的视野里才是一样的存在。其次才是民事行为能力的平等,凡年龄和心智达到一定标准者均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反映到分则中,则是财产权享有和保护上的平等、契约主体地位的平等、契约自由和公平、婚姻自由和男女平等、遗嘱自由和继承权平等保护。
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一律平等,不因其性别、年龄、民族、职务、文化程度等方面的差异而存在区别,都有平等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资格。若外国人需要与我国公民享有平等的民事权利能力,一般需要其所属国家对等地给予我国公民国民待遇。无国籍人在我国领域内实施民事活动,也与我国公民享有平等的民事权利能力。
自然人权利能力平等是民法赖以生存的市民社会的本质特征,也是近代私法的重要进步。人的权利能力平等在今日被认为理所当然,然而,在当时的西欧历史上,却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事件。古罗马法上以身份决定人格,故人与人之间的人格是不平等的,古罗马法的平等只是在作为家长的男性罗马市民中才具有的原则,女性、家子、奴隶都不具有人格或人格减等,并不是平等原则考虑的对象。
中世纪时期的人依其性别、身份、所属职业团体和宗教的差异而不同,分为非自由人(奴隶、半自由人如降服民族及其子孙)和自由人(农奴、自由农、区属、贵族)。在家庭内部,各成员间地位也非平等,身份等级森严的特点非常鲜明。
随着启蒙运动的深入和对人类理性的尊重,任何具有完全理性的人在地位上均应当被平等对待成为共识,1804年《法国民法典》将自然法所倡导的无差别的“人类理性”作为实定法上的人格取得依据,从而使“生而平等”的伦理价值观念在法典上得以落实。
古代中国长期处于“三纲”“名教”统摄之下,形成的是义务本位的法观念,缺乏权利本位观念。甲午战争之后,维新派把天赋人权的思想具体化为天赋的自由权和平等权,康有为、谭嗣同、严复等对这一观念大加推广,使法观念不断变革,并集中体现在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的一系列立法实践中。[1]国民党政府颁布的《中华民国民法》(1949年废止)中,规定“人之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直至原《民法通则》颁行,我国私法领域第一次开宗明义规定“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一律平等”。
自然人权利能力是否一律平等,在我国民法理论界素有争议。在原《民法总则》起草过程中,多个版本的草案建议稿中均主张写明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平等,但也有学者对此持不同观点。有的学者指出:“自然人的权利能力范围实际上有大有小,如结婚权利能力,并非人皆有之”,“可将权利能力做一般和特别之分。”[2]也有学者指出,自然人的权利能力根本不可能平等。公民与外国人、农村与城市人以及此城人与彼城人、被监禁者与自由人、失权人与全权人、军人与平民、出家人与在家人、健康人与患有特定疾病者,在能力上均有差别,如何还能坚持认为自然人权利能力平等呢?因此,如若规定自然人权利能力平等,应该增加“自然人的权利能力平等,但受立法、司法剥夺者除外”。
对上述观点,试做如下评述:其一,鉴于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与法律人格的高度关联,“对于平等原则应从法律伦理价值的角度去理解,而不能机械地理解”;其二,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是一种“起点平等”,上述认为权利能力有大有小的观点实际上“混淆了作为取得权利资格的平等与具体取得的权利的平等之间的差异”;其三,实践中许多对人之行为范围的限制,是基于某种价值判断或者国家政策对自然人行为的限制而非对其“权利能力”的限制。[3]故此,本条规定的民事权利能力,其所指仅为抽象意义上享有法律允许享有的一切权利(权利之总和)的资格,而非具体意义上的特定资格。故“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一律平等”成为本法的基本原则。
适用指引
域外自然人、无国籍人的民事权利能力认定
在国际私法上,对于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的适用,基本上都以“属人法”来确定,“属人法”相关的地域因素主要有籍贯、住所、国籍、居所等,这些都是“属人法”的连接点。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12条第1款规定,自然人的民事行为能力,适用经常居住地法律。可见,我国立法采取的是“属人法”中的“住所地法主义”。这对于具有“一国两制四法域”特点的我国而言,是解决区际私法冲突最具可操作性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