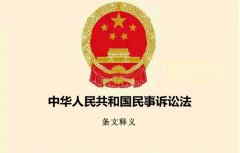第一千零八十五条 【离婚后子女抚养费的负担】离婚后,子女由一方直接抚养的,另一方应当负担部分或者全部抚养费。负担费用的多少和期限的长短,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
本条源自2001年修正的原《婚姻法》第37条,该条规定:“离婚后,一方抚养的子女,另一方应负担必要的生活费和教育费的一部或全部,负担费用的多少和期限的长短,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关于子女生活费和教育费的协议或判决,不妨碍子女在必要时向父母任何一方提出超过协议或判决原定数额的合理要求。”
2018年3月《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征求意见稿)》第44条延续了2001年修正的原《婚姻法》第37条的基本内容,只是将“必要的生活费和教育费”修改为“必要的抚养费”。
2018年8月《民法典各分编(草案征求意见稿)》第862条则将“必要的抚养费”修改为“抚养费”。后本条内容除了有个别文字、语序调整外,再无实质变化,直至《民法典》正式颁布。
(一)子女对父母享有法定的抚养费请求权
与大部分民事法律关系不同的是,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是基于法律的直接规定,因子女的出生事实、收养行为或抚养教育而产生。
《民法典》第1084条第1款和第2款规定,父母与子女间的关系,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
离婚后,父母对于子女仍有抚养、教育、保护的权利和义务。
即父母对子女负有基于法律的直接规定而产生的法定义务。这种义务既有人身属性,又有财产属性,且不附加任何条件,不因夫妻双方之间婚姻存续状态的变化而变化,它是子女抚养费请求权的基础。
我国原《婚姻法》从1980年起,也采取了类似的规定方式。
需要注意的是,抚养费请求权是作为被抚养对象的子女依法享有的权利。它与夫妻双方的婚姻关系状态,夫妻之间对于抚养费的分担约定等因素并无必然联系。父母对子女的抚养义务不能因离婚而得以免除。
即使在父母协议约定由一方承担子女的全部抚养费的情形下,另一方虽按约定可不承担支付抚养费的义务,但对子女仍负有抚养的责任,子女依旧得在必要时向其主张抚养费请求权。
之所以对离婚后父母对子女的抚养费分担予以特别规定,是因为一般情况下,在夫妻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对子女的抚养由夫妻双方共同进行,尤其在夫妻共同财产制之下,抚养费的分担并无明显区分。
离婚后,直接对子女进行抚养、教育、保护的义务主要由父母中的一方承担,另一方对子女的抚养义务则多直接表现为抚养费的支付。
此时,在已不存在共同财产的情况下,父母对子女的抚养费明确分担义务,一方面事关父母双方是否对子女尽到抚养义务,另一方面对保障未成年子女的健康成长或不能独立生活子女的生存权亦具有重要意义。
本条第2款规定即体现了这种考量,抚养费保障子女的健康成长和生存权利的基本功能,决定了离婚后父母对子女抚养费的给付,不能以双方间的协议或法院的判决而就此固定。
从开始给付抚养费到客观上无须继续履行给付义务,常常会经历比较长的时间跨度。
社会经济条件和子女对教育、医疗等的需求变化,都可能导致先前确定的抚养费金额甚至期限不足以覆盖子女的现实需求。这种情况下,应当允许子女在合理范围内向父母主张增加给付或继续给付抚养费。
(二)准确界定抚养费的范围
2001年修正的原《婚姻法》第37条将父母支付的费用笼统列举为“必要的生活费和教育费”,与该法第21条第2款“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时,未成年的或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有要求父母付给抚养费的权利”中采用“抚养费”的表述方式有所区分。
未成年或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要求父母给付抚养费,是法律规定赋予子女的权利。这种抚养费请求权的基础是父母子女关系,不受父母的婚姻关系是否继续存续的影响。
原《婚姻法》这种前后表述的不一致,实际上产生了父母的婚姻关系存续状态影响子女抚养费请求权的后果。
审判实践虽可以根据案件情况作一定的扩大解释,但法律条文上的偏差仍应当纠正。为此,本条取消了2001年修正的原《婚姻法》第37条的表述,改为“抚养费”,与《民法典》第1067条规定保持一致,体系上更加顺畅。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42条将抚养费定义为“包括子女生活费、教育费、医疗费等费用”,明确了生活费、教育费、医疗费是父母支付的抚养费应有的内容。立法设置抚养费制度,究其目的是保障子女的健康成长。
《
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6条第5项、第28条、第83条规定,未成年人享有受教育权,国家、社会、学校和家庭尊重和保障未成年人的受教育权。
《
义务教育法》第5条第2款规定,适龄儿童、少年的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当依法保证其按时入学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
受教育权是未成年子女的法定权利,让未成年子女接受教育也是父母的法定义务。
生活费、教育费、医疗费作为保障子女基本生活和智能、身体均衡发展的基本条件,必须涵盖在抚养费的范围之内。
但是,子女的抚养费请求权并不限于以上三种,当产生对子女的健康成长合理必要的其他费用时,父母同样应当履行支付义务。
本条在条文表述上未对抚养费的种类范围予以具体限制,给予父母双方或人民法院在协商自愿或需求合理的情况下扩大给付范围的空间。这既有利于子女权利的保护,也更符合社会生活不断变化的实际要求。
(三)抚养费的分担原则和确定标准
1991年,我国批准了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其中第3条第1款规定,关于儿童的一切行动,不论是由公私社会福利机构、法院、行政当局或立法机构执行,均应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一种首要考虑。尊重和保护儿童利益,已成为国际社会普遍认可和接受的通识。
《意大利民法典》在其条文中,多处体现了保护子女利益的立法倾向,如法官应充分考虑到(父母)分居可能给子女带来的精神和物质利益影响,在宣布分居时要同时确定将子女判给父母一方抚养以及其他所有为子女的利益而采取的措施。
夫妻协议分居时,如果分居协议中有关子女抚养或抚养费的规定与子女利益不相符,法官可以召集配偶双方为子女利益进行修改;仍不适宜时,法官可以拒绝修改。
《民法典》颁布前,有学者认为,以监护人的确定为例,我国法律多以父母的利益或意愿为优先,对子女的利益缺乏考虑,建议将“未成年子女最大利益原则”写入条文予以明确,同时主张,应当将子女最大利益的审酌因素确定为:
(1)子女的年龄、性别、人数及健康状况;
(2)子女本人的意愿与人格发展的需要;
(3)父母的年龄、职业、品行、健康状况、经济能力等生活状况;
(4)父母保护教养子女的意愿与态度;
(5)父母子女间或者未成年子女与其他共同生活者之间的感情状况。
离婚后子女抚养费的分担和确定问题亦是如此,婚姻关系的结束消灭的是夫妻关系,但不影响父母子女关系,不意味着父母对子女抚养义务的消灭,无论是否直接抚养子女,概莫能外。
对人民法院来说,当夫妻双方无法通过自行协商确定子女抚养费的分担,需要借助司法权确定抚养费的给付时,人民法院对抚养费分担的裁判,应当以子女最大利益为首要的考量因素。
具体而言,抚养费的分担需考量以下因素:
(1)满足子女的生活、教育、医疗等方面的需要;
(2)符合当地的实际生活水平;
(3)父母双方根据各自实际负担能力合理分担。
审判实践中,人民法院可能会遇到父母双方经济条件相差较大,离婚后子女的生活环境、生活条件将发生较大变化的情况。
此时,人民法院应当在尽量保护子女利益的基础上,尽可能使抚养费既能满足子女的实际需要,又不至于给父母双方造成过重负担或使抚养费成为变相的财产分割手段,使父母双方得以适当、均衡负担。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49条规定:“抚养费的数额,可以根据子女的实际需要、父母双方的负担能力和当地的实际生活水平确定。有固定收入的,抚养费一般可以按其月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比例给付。
负担两个以上子女抚养费的,比例可以适当提高,但一般不得超过月总收入的百分之五十。
无固定收入的,抚养费的数额可以依据当年总收入或者同行业平均收入,参照上述比例确定。有特殊情况的,可以适当提高或者降低上述比例。”第53条规定了抚养费的给付期限,一般至子女18周岁为止。
16周岁以上不满18周岁,以其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并能维持当地一般生活水平的,父母可停止给付抚养费。
同时对子女虽已成年,但仍有给付抚养费必要的情形也作出了规定,即第58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子女要求有负担能力的父或者母增加抚养费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一)原定抚养费数额不足以维持当地实际生活水平;
(二)因子女患病、上学,实际需要已超过原定数额;
(三)有其他正当理由应当增加。”
与此同时,该解释第50条还规定,抚养费原则上应当定期给付,父母条件允许的也可一次性支付。
就何种情形下抚养费可以一次性支付,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在对原《婚姻法》的释义中认为,一次性给付的要慎重处理,确有必要采取一次性给付的,要注意掌握条件:
一是出国、出境人员;
二是有能力一次性支付的个体工商户、专业承包户、私营企业业主等人员;
三是下落不明的一方以财产折抵的;四是双方自愿、协商一致的。审判实践中,人民法院在参考以上情形的前提下,仍应当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况,结合实际妥善处理。
(四)抚养费的变更
本条第2款规定赋予了子女在“必要”时,向父母请求“合理”数额的超出原协议或判决的抚养费的权利。
离婚后子女抚养费负担方案的确定,是基于当时的社会经济水平、父母的负担能力、子女的需求等因素而作出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物价水平的变化、子女个体情况的变化、父母收入水平等的变化,原抚养费数额、给付方式、给付期限等均有可能发生不再适应子女的需求或父母的负担能力的情况。
尤其是当直接抚养子女一方的经济水平不足以维持子女的基本生活、教育、医疗等方面的需求时,必须允许子女向不直接抚养的一方提出超过原协议或判决的抚养费请求。
这也是父母共同对子女承担抚养责任的要求,与该方原来负担抚养费的多寡,是否实际履行支付抚养费义务均没有关系。
但是,子女提出的抚养费请求必须合理。如果其请求的数额已经明显超出了必要、合理的范围,人民法院依法不予支持。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58条对何为“必要”规定了三种情形,包括:
(1)原定抚养费数额不足以维持当地实际生活水平的;
(2)因子女患病、上学,实际需要已超过原定数额的;
(3)有其他正当理由应当增加的。
有意见认为,“在必要时提出超过原定数额的合理请求”指向的是不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必要时向父母任何一方提出超过协议或者判决原定数额的合理要求”的表述,既可以指向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也可以指向不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并不妥当。
实践中,抚养费的变更大多数可能发生于子女与不直接抚养的一方之间。但是,多数情况的存在,并不能完全排除直接抚养子女一方未尽到抚养义务的情形。从子女最大利益原则的角度出发,亦不能剥夺子女的此种权利。父母双方对子女的抚养义务,理当共同承担。“
向父母任何一方提出”的表述,再次强调了抚养义务的共同性,比之规定子女向不直接抚养的一方主张抚养费的表述,更为全面。
对此,《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43条也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父母双方或者一方拒不履行抚养子女义务,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请求支付抚养费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适用指引
司法实务中,一种观点认为,子女可在必要时向父母任何一方提出超过协议或者判决原定数额的合理要求,并不意味着抚养费的变更请求只能由子女本人提出,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亦可提出该种请求。
抚养费具有保障被抚养子女正常生活和成长的属性,关涉子女的合法权益,在子女本人之外,允许直接承担对子女的抚养、教育、保护义务的一方代子女请求,并不会改变抚养费的权利主体,从实践上看,更有利于子女合法权益的保护。
我们认为,根据《
民事诉讼法》第122条规定,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而直接抚养子女一方只与子女所主张的抚养费有间接利害关系,不能作为原告主张子女抚养费,而只能以代理人身份提出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