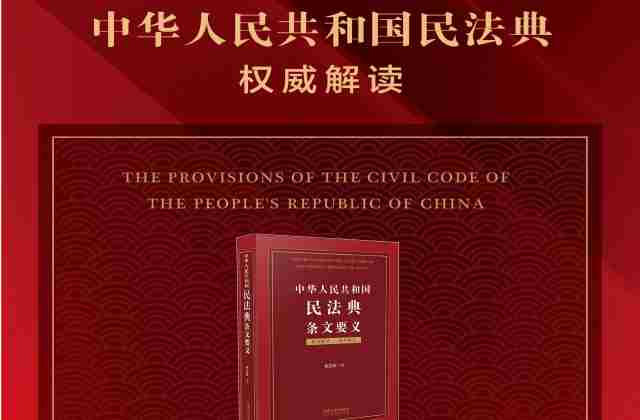原《民法通则》对侵权责任制度的调整范围没有直接作出规定,但该法第106条第2款、第3款,对于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行为,作出了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对于没有过错,但法律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上述行为,也规定了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根据这两条规定,可以推论出侵权责任制度的调整范围,是侵害民事主体的人身和财产权益所产生的侵权法律关系。
原《侵权责任法》第2条第1款规定:“侵害民事权益,应当依照本法承担侵权责任”,从侵权法律关系客体范围的角度明确了侵权责任法的调整范围,但未采取从法律关系角度予以规范的定义方式。第2款对受原《侵权责任法》保护的民事权益,按照“列举加概括”的方式作了不完全列举,涉及范围广泛的民事权益,但其所列举的民事权益均属具有对世性的人身、财产权益,揭示了侵权法律制度保护的民事权益原则上是具有对世性的绝对权这一特征。
《民法典》本条规定在侵权责任编第一章“一般规定”中,是从法律关系的角度作出规定,与原《侵权责任法》第2条第1款从权益保护角度作出规定不同,立法技术上继承了我国民事立法一般从法律关系角度定义调整范围的传统,且与《民法典》各编调整范围的规定在立法体例上保持一致。
本条规定了侵权责任编的调整范围,即“因侵害民事权益产生的民事关系”。关于侵害民事权益产生的民事关系,在《民法典》第120条关于侵权责任请求权的条文解读中已作梳理,故本条重点梳理作为调整对象的“民事权益”内容及其法律特征。
(一)侵权责任编保护的民事权益的概念
民事权益,是指民事权利和民事利益。利益,是指对民事主体精神和物质需求与欲望的满足,故利益本身是一个中性概念,因其可能具有正当与不正当的属性而区分为合法利益与非法利益。受法律所保护的民事利益应当具有合法性,因而是合法利益。权利就其满足权利主体物质和精神需求的意义而言,本质上也是利益,但其不同于利益的基本特征,在于法律明确赋予其权利属性,并以国家强制力作后盾保障权利享有者依法实现其权利。因此,民事权利就是指为了保护民事主体的特定利益而赋予民事主体可以享受该特定利益的法律上之力。它包含三个特征:
第一,利益的类型化,即有名性(或曰公示性),在逻辑上特定利益被归属于排他性[1]的概念范畴,如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隐私权、姓名权、名誉权等。
第二,利益的法定化,即法定性,立法将类型化的特定利益以明确的权利概念规定在法律中。故未经法律确认为民事权利的利益,虽具正当性,可以视为合法利益,但不属于民事权利。
第三,实现的强制性,即法律对民事主体实现民事权利赋予终局的强制力保障。支配权可以直接行使,遇有妨碍、阻止的情形可以请求公权力予以排除。请求权亦可径行主张,相对方不履行的则可请求公权力机关依法裁决后申请强制执行。
这三项特征,作为民事权利是同时具备的,而民事利益通常不具备或者不完全具备这三项特征。例如,“纯粹经济损失”,就是对人身、财产损害以外的经济上的不利益的一种概括、泛化的指称,其内涵不统一,外延不确定,误工工资、合同履行利益、额外费用支出等,均可为纯粹经济损失,难以在概念范畴上予以类型化,因而其在技术上不能被确认为民事权利而只是一种民事利益。个人信息[2],亦具有类似特征,因而在《民法典》人格权编之第六章,个人信息与隐私权并列,但并未被规定为民事权利,解释上认定其为一种民事利益。
民事利益虽不同时具备民事权利的上述三项特征,但并不意味着民事利益不受法律保护。《民法典》第1034条明确规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
个人信息保护法》更以单行法的形式,对个人信息的收集、存储、使用、加工、传输、提供、公开、删除等个人信息处理制定了明确的规则,以保护个人信息权益享有者的合法权益。该法第69条第1款规定:“处理个人信息侵害个人信息权益造成损害,个人信息处理者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等侵权责任。”明确了侵害个人信息相关民事利益也要承担侵权责任。但由于民事利益通常具有广泛性和缺乏外部公示性(有名性)的特征,除了少数法律列举的民事利益(如个人信息,死者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等)外,民事利益的保护通常需要在个案中进行甄别,判断其是否符合以下三项标准:
第一,合法性。对于法律有明确规定的民事利益,其合法性自然毋庸置疑。对那些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利益,如何判断其合法性?一般可以有如下判断标准:(1)取得合法或者来源合法;(2)内容正当,即不违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违反公序良俗;(3)不损害他人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
第二,私益性。即该项利益归属于特定民事主体,非属公共利益。一种观点认为,侵权法保护的利益应当是私法上的、具有绝对性的合法利益,对此,应当辨明,此之所谓“私法上”的利益不能理解为只有私法上规定的利益才能被视为具有私益性的利益。一些指向个人的保护性法律规范可能是社会保障法或者有关行政法等公法上的规定,但其公法保护作用的反射性结果,实际上指向了私人利益。
第三,可救济性。可救济性是指救济的必要性与救济的可能性。(1)救济的必要性是指对该正当利益的侵害达到违反公序良俗的程度,不予司法救济将导致严重的利益失衡,且不能通过其他间接方式获得司法救济(例如,因遭受性侵、猥亵等主张贞操利益受到侵害的,可以通过身体权、健康权、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等权利侵害的救济渠道获得救济)。因此,对于一些情节轻微,不致严重影响或者过度妨碍正常生产、生活的情形,无须通过司法救济途径予以救济。(2)救济的可能性是指符合《
民事诉讼法》第122条规定的起诉条件,具有诉的利益。
不符合上述三项标准,即不能被甄别、判断为受民事法律所保护的民事权益。故民事权利的法律保护是应然的,民事利益则区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情形是在民事法律规范中已经明确的民事利益,其司法保护没有疑义,也是应然的;另一种情形则是法律没有明确规定,而是在社会生活中实际存在和发生的民事利益,因其具有广泛性、开放性、发展变化性和性质复杂性(有正当利益与不正当利益之别),故其司法保护须在符合上述三项特征的前提下进行甄别、判断,以确定其是否应当受法律保护。
(二)侵权责任编保护的民事权益的特征
侵权责任法律制度的调整范围是民事权益,但并不是所有的民事权益都受侵权责任法律制度的保护。理论上认为,侵权法的保护范围是民事权益中的绝对权和具有绝对权性质的民事利益。
绝对权是指请求一般人不为一定行为之权利,亦即请求世人勿侵害其权利之权利,故亦称“对世权”。其特征:一是义务人不确定,任何人皆负有不得侵害权利人之权利的义务;二是义务人所负义务的内容是不作为,即权利人无须通过义务人实施一定的积极协助行为即可实现其权利。人格权、物权、知识产权均属之。与绝对权对应的是相对权,是指请求特定人为一定行为或者不为一定行为之权利。其特征:一是义务人特定,权利人仅能针对特定人主张权利,故又称“对人权”;二是义务的内容是应权利人的请求为一定行为或者不为一定行为(不作为)。债权即属相对权。
民法理论将侵权法的保护范围限于绝对权益,是基于如下的法律政策考量:侵权法的基本功能之一是在民事主体的民事权益保护和行为人的行为自由之间达到合理的价值平衡。因此,近代以来确立的一般侵权的归责原则为过错责任原则:有过错则承担责任,无过错则不承担责任(后来发展起来的无过错责任原则除外,无过错责任原则适用于特殊侵权行为,以法律有特别规定的为限,其不以过错为侵权成立的构成要件,强化了诸如环境保护、产品生产和销售、高度危险以及机动车交通事故领域的侵权责任,但在保护绝对权益方面与一般侵权行为并无二致),过错被确定为承担侵权责任的理性主义侵权法的基石。过错意味着对注意义务的违反。绝对权的性质,决定了权利人以外的所有人都负有尊重权利人的权利的注意义务,因而因过错违反注意义务造成损害的,就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而相对权以相对性为其基本特征,即通常不对相对人以外的第三人公示其权利,亦无须向相对人以外的第三人主张权利,其权利实现端赖相对人对义务的履行而与其他人无关。由于权利的相对性阻断了相对人以外的第三人对权利的认知,权利的实现也无须相对人以外的任何其他人的介入,相对人以外的第三人也不负有对权利人行使权利和实现其权利的注意义务。对不知道或者不应当知道其权利存在的第三人课以注意义务,是不合理的,违反理性原则,会导致行为人陷入不可预知的责任陷阱,从根本上妨碍行为人的行为自由。而无义务则不产生因违反义务所生责任。
因此,第三人因过错而导致相对权人的权利损害就不承担侵权责任。例如,A驾车不慎,撞伤将在B歌厅作个人秀的歌星C时,对C身体健康受侵害而生的损害(财产上损害或非财产上损害),固应负赔偿责任,但对B歌厅因辍演所受的损失,则不必负赔偿责任。否则A的责任范围,将漫无边际,诚非合理。[4]其理由就在于,C身体健康所受侵害为绝对权益所受侵害,其所生损害得依侵权责任法主张赔偿;而B歌厅因C受伤辍演所生损害系因A的行为造成其债务人受伤致合同履行不能所受损害,系第三人造成的债权即相对权益受损,但A并不知晓B与C之间的演出合同关系,则无论其因故意或者过失造成C受伤,B均不能提起侵权之诉,主张A承担因C受伤辍演致其蒙受纯粹经济损失的损害赔偿责任。
不仅民事权利,民事利益亦仅在具有对世性的前提下,才能成为侵权法的保护客体。个人信息作为民事利益,具有对世性;死者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等民事利益,同样具有对世性;故对个人信息及死者姓名等民事利益,任何人均不得非法侵害。
基于上述,《民法典》侵权责任编保护的民事权益,具有绝对权益的性质,即具有对世性。债权系指特定人得向特定人请求为特定行为的权利,不具对抗第三人的效力;第三人既不负债务,自无侵害的可能。[5]故一般而言,债权权益不在侵权责任法的保护范围之内。在绝对权与相对权的分类体系中,侵权责任法原则上保护绝对权益,相对权仅在对第三人满足类似于绝对权益对世性特征的特定情形下(突破相对性而为第三人所知悉),且不能通过相对权法律保护途径本身获得救济时,才例外地纳入侵权责任制度的保护范围。
应当注意的是,《民法典》第186条规定:“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损害对方人身权益、财产权益的,受损害方有权选择请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侵权责任。”依据该规定,在发生侵权责任与违约责任竞合的情形,受损害方有请求对方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侵权责任的权利,但该条规定的适用范围,限于违约行为造成对方人身权益、财产权益损害的情形,而此之所谓人身权益和财产权益,是指具有绝对权性质的人身、财产权益,理论上称为“固有权利”或者“维持利益”。因违约导致的纯粹经济损失,属相对权益性质的履行利益范畴,则只能通过违约责任主张损害赔偿。因此,《民法典》第186条的规定,并未改变侵权责任法保护的客体范围是具有绝对权性质的民事权益这一基本特征。
(三)侵权责任编保护的民事权益的范围
侵权责任制度保护的民事权益的范围,在原《侵权责任法》中曾作过列举加概括式的规定。原《侵权责任法》第2条第2款规定:“本法所称民事权益,包括生命权、健康权、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监护权、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著作权、专利权、商标专用权、发现权、股权、继承权等人身、财产权益。”上述条款列举的民事权益,其共性特征为对世性,而不包含相对权性质的债权。实际上隐含了侵权责任法律制度所保护的民事权益是绝对权性质的民事权益的思想,而并非所有的民事权益。
《民法典》侵权责任编在本条规定中没有列举侵权责任编保护的民事权益的具体类型,这是因为《民法典》具有体系化构造的立法特征,需要结合总则编“民事权利”章和各分编的具体权利规定作出系统解释。
概括来说,侵权责任法律制度所保护的民事权益具体包含人身权益和财产权益两个方面。
1.关于人身权
理论上又区分为人格权和身份权。
人格权,是指自然人等民事主体对与其特定人格直接相联系的生命、身体、健康、姓名、名称、肖像、名誉、荣誉、隐私等利益所享有的权利。人格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尊严与资格。人格权的基本特征,是其与特定民事主体的人格不可分离(如不得转让、继承等)且没有直接财产内容。
按照《民法典》总则编第五章的规定,自然人的人格权可以区分为一般人格权与具体人格权。一般人格权是指自然人的“人身自由、人格尊严”(第109条)。具体人格权在理论上又区分为物质性人格权与精神性人格权,前者是指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后者是指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等(第110条第1款)。与自然人的人格权相对应,法人、非法人组织享有名称权、名誉权和荣誉权(第110条第2款)。
身份权,是指对基于亲属关系产生的身份利益所享有的权利。理论上对我国法律规定的身份权有不同的梳理[6],但作为侵权责任法律制度保护范围的身份权通常是指监护权与亲权(第1068条等,但我国民事法律未使用“亲权”概念,而直接以内容揭示权利即“父母有教育、保护未成年子女的权利和义务”)。继承权被侵害,通常通过物权请求权与债权请求权的方式获得救济。
2.关于财产权
按照总则编第五章“民事权利”的规定,民事主体的财产权利,包括第114条的物权,第118条的债权,第123条的知识产权,第124条的继承权,第125条的股权和其他投资性权利,第127条的数据、网络虚拟财产权。
上述财产权利,既有绝对权性质的物权、知识产权,也有相对权性质的债权。“民事权利”章第120条规定:“民事权益受到侵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该条规定的“民事权益”概念,并未排除债权,相反,依据逻辑和体系解释,是明确包括债权在内的(同一章中的种、属概念,逻辑上存在包含关系),因此债权依法属于侵权责任制度的保护范围。本条(第1164条)规定“本编调整因侵害民事权益产生的民事关系”,依据概念的同一性原理,此之所谓“民事权益”当然也包括债权。前述侵权责任制度保护的民事权益的特征,原则上为绝对权,这是否与《民法典》的规定存在冲突呢?前文已阐明,从一般侵权责任的角度观察,行为人对他人主观权利的存在应负注意义务,但如果该项主观权利乃是相对的,不为第三人所知的,则对该第三人而言,该主观权利并不存在,其亦无从预见并加以注意。如果行为人无法预见或者无法避免损害的发生,他就没有过错,不应当为损害后果负责。如果行为人尽了最大的注意义务,仍不能预见行为的后果,那么,该后果就并非行为意志自由的产物,要求行为人为此负责,显非合理。[7]但是,相对权之相对性是依其性质而论,并非依据事实而论。实际生活中,债权的相对性可能被克服,而为第三人所知,从而对于该第三人具有了一定程度的绝对权的性质,例如房屋买卖合同因网签而具有了公示性,克服了相对性。在此情形下,第三人同样负有不得侵害债权的注意义务,如果故意介入债务的履行并加以阻碍(例如故意驾车撞伤赴演出途中的演员,致演出取消),即构成第三人侵害债权,对债权人遭受到的纯粹经济损失,应负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因此,将债权纳入侵权责任制度的保护范围,并未改变侵权责任制度的保护范围是具有对世性的绝对权权益的特征,而是使侵权责任制度的保护范围更加周延。
对侵权责任编保护的民事利益的范围,《民法典》没有系统列举,而是散见于总则编“民事权利”章及分则各编的规定中,如第185条对英雄烈士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的保护,第994条对死者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隐私、遗体等利益的保护,第1023条第2款“对自然人声音的保护”,均属之;此外,第126条的“其他民事利益”,也提供了概括的指引,即凡具有绝对权益性质并受到法律保护的民事权益,均属之,如《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9条规定的“商业秘密”等。
适用指引
一、关于侵害身体权作为请求权基础的司法适用
《民法典》在第110条规定的具体人格权中,首次列入“身体权”,进一步完善了人格权保护的法律体系。
从司法保护的角度看,2001年《精神损害赔偿解释》第1条第1项[8]列举了身体权,是通过对原《民法通则》第98条和第119条的解释适用引申出的独立的保护客体。原《侵权责任法》制定时,没有吸收
司法解释的规定。因为我国传统的民法理论将“身体”解释为生命权和健康权的物质载体,没有独立性,立法囿于传统理论,未能突破旧有的规定。司法实践中身体法益受到侵害但并未造成健康受损的情形客观存在,最终促使《民法典》将身体权作为独立的具体人格权予以规定,在立法和审判实务中都具有重要意义。
从立法上看,《民法典》第994条对死者遗体的保护,显然是自然人身体法益的延伸保护。没有独立的身体权,难以有延伸的身体法益即对“遗体”的保护;同样,第1006条对人体细胞、人体组织、人体器官的保护也会落空,因为这些人格利益都是包含在身体权的法益当中的。没有独立的身体权,立法对上述身体法益的保护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民法典》将“身体权”作为独立的民事权利予以规定,不仅完善了人格权的法律体系,而且为今后涉身体法益案件的处理提供了请求权基础和法律依据。
二、关于胎儿利益纳入侵权责任法保护范围的司法适用
关于胎儿利益的保护,《民法典》第16条规定:“涉及遗产继承、接受赠与等胎儿利益保护的,胎儿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但是,胎儿娩出时为死体的,其民事权利能力自始不存在。”对该条规定的立法意旨,存在不同理解,有观点认为该条规定系采对胎儿利益总括保护主义立法模式[9],亦有主张其仍属个别保护主义立法模式[10],从条文具体列举继承、接受赠与等胎儿民事利益的表达技术来看,应属个别保护主义的立法模式[11],但“本条用了一个‘等’字,没有限定在继承范围以内,原则上也包括侵权等其他需要保护胎儿利益的情形”[12],实际上是较为弹性的规定,赋予了司法机关根据“需要保护胎儿利益”的立法目的予以解释适用的空间,与总括保护主义的立法模式结果上并无二致。因此,胎儿于母体内受胎发育之身体及其健康状况,属于第16条规定的需要保护的胎儿利益,即属于侵权责任编规定的民事权益范围,该项利益所受损害可以依据侵权责任编的规定获得保护。
在司法实务中需要明确的是,胎儿利益的保护如何在程序上实现?过去的实践中有将胎儿视为母亲身体的一部分,而对胎儿在母体内所受伤害由母亲作为权利主体概括予以主张,即在民事诉讼中仅列母亲为原告。《民法典》规定胎儿就其利益保护视为具有权利能力,即肯定其可以作为独立的民事主体主张权益保护,而无须将其视作母亲身体的一部分,通过母亲的权益诉求获得反射性保护。因此,在侵权民事诉讼中,可列其为当事人,而由父母作为其法定代理人。
在理论上,对胎儿权利能力的性质,存在两种不同的学说。其一为附解除条件说。该说认为胎儿出生前即已取得权利能力,但将来如系死产时,则溯及丧失其权利能力。其二是附停止条件说,认为胎儿须待出生后,始溯及出生前取得权利能力。两说在实务上的区别,依前说则胎儿因他人故意或者过失行为遭受损害,即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可由胎儿的父母以法定代理人的身份请求损害赔偿。胎儿娩出后为死体的,因其自始不享有权利能力,故其父母应依不当得利的规定返还以胎儿名义受领的损害赔偿。依后说则认为须待胎儿出生后不即死亡的,方能就其出生前所受侵害行使损害赔偿请求权。[13]《民法典》第16条规定,胎儿出生前被“视为”具有权利能力,“视为”乃法律上的拟制或推定,故胎儿不待其出生就其利益保护事项即享有权利能力,仅当其娩出时为死体的,权利能力自始不存在。显然,《民法典》的规定符合附解除条件说的原理,故胎儿可就侵权所造成的利益损害以自己的名义主张损害赔偿,其父母则以法定代理人身份代理其请求。
依据附解除条件说,可以对基于同一侵权事实造成的人身损害合并进行审理,有利于胎儿出生后及时得到救济,符合诉讼经济和诉讼效率原则。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是,如胎儿娩出时为死体的,已判决的损害赔偿金应当如何处理?一种观点认为因胎儿娩出时为死体,其权利能力自始不存在,故应将损害赔偿金视为不当得利返还侵权人;另一观点则主张,判决的损害赔偿金可以不即给付,而向人民法院或公证机关提存,胎儿出生后存活的,依据生效判决执行;胎儿娩出时为死体的,可由提存机关依据法院裁定将提存的损害赔偿金直接返还给赔偿义务人,避免不当得利返还所可能发生的纠纷。[14]但存在的问题是,生效判决的既判力约束如何解决?另外,如果有证据证明胎儿娩出时死亡与侵权行为有关,胎儿父母主张此种情形应视为母体所受损害,损害赔偿金应终局归属于母亲,而无须返还,又应当如何处理?均值得审判实践中进一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