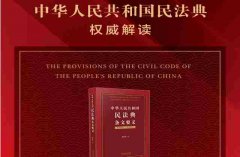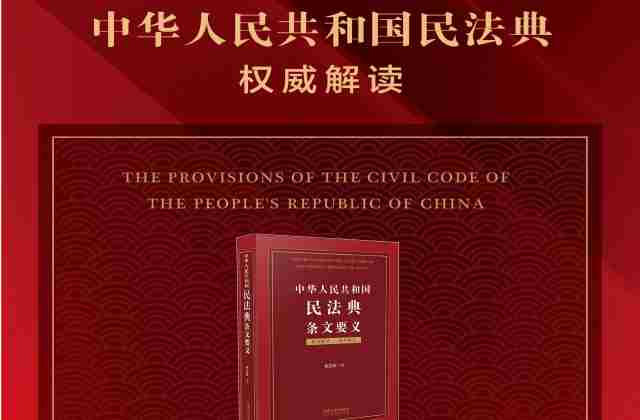(一)探矿权、采矿权
法律层面上,探矿权、采矿权最早出现在1986年的《
矿产资源法》中,但未明确其权利属性。
1986年颁布的原《民法通则》第81条第2款规定:“国家所有的矿藏,可以依法由全民所有制单位和集体所有制单位开采,也可以依法由公民采挖。
国家保护合法的采矿权。”由此,确定了采矿权的财产权属性,但没有明确探矿权的财产权属性。2017年公布实施的原《民法总则》删除了原《民法通则》中关于采矿权的相关规定。
《民法典》除本条规定外,亦未再有涉及探矿权、采矿权的相关规定,但探矿权、采矿权的概念频繁出现在相关行政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中。
如1994年《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第6条对探矿权、采矿权作出了明确的定义:“探矿权,是指在依法取得的勘查许可证规定的范围内,勘查矿产资源的权利。”
“采矿权,是指在依法取得的采矿许可证规定的范围内,开采矿产资源和获得所开采的矿产品的权利。”
原国土资源部2000年颁布的《矿业权出让转让管理暂行规定》第3条规定:“探矿权、采矿权为财产权,统称为矿业权,适用于不动产
法律法规的调整原则。”“依法取得矿业权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称为矿业权人。”
“矿业权人依法对其矿业权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权。”
关于探矿权、采矿权的性质,法学界基于不同的学术背景、学科视野和实践经验各自作出了不同的评价。
经济法学者、环境资源法学者以及行政法学者,更侧重于矿业权配置的国家干预性,大多提出公法权力与私法权利综合调整兼具之说。民法学界内部,亦存在物权化债权说、用益物权说、准物权说、准用益物权说、特别物权说、特许物权说等不同观点。
就法律规定而言,本条关于“依法取得的探矿权、采矿权受法律保护”设置在物权编用益物权分编下的一般规定中,从法解释学的角度可认为探矿权、采矿权的属性为用益物权。但值得注意的是,《矿产资源法》第3条规定:“……勘查、开采矿产资源,必须依法分别申请、经批准设立探矿权、采矿权,并办理登记……”
《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第5条第1款规定:“国家对矿产资源的勘查、开采实行许可证制度。勘查矿产资源,必须依法申请登记,领取勘查许可证,取得探矿权;开采矿产资源,必须依法申请登记,领取采矿许可证,取得采矿权。”由此,在我国现行法律框架内,探矿权、采矿权是一种矿产资源用益物权,但其设立须经政府审批、行政许可,具有强烈的公法属性,作为矿业权物权凭证的矿产资源勘查许可证和采矿许可证,同时亦是国土资源主管部门作出行政许可的法律文书。由此,矿业权兼具民事物权和行政许可的双重属性。
一方面,所有权人可以通过与他人签订合同享有债权的方式享受利益,也可以通过设立他物权的方式来享受利益。矿业权就是作为所有权人的国家所设立的一种他物权,是矿产资源所有权让渡权能的结果。
另一方面,行政许可是引起矿业权民事法律关系成立之必要的事实行为,行政许可或者特许起“催生”“准生”与确认的作用,赋予行为人以法律上之力,使其占有、使用等状态名实相符。
作为矿产资源国家所有权基础上派生出来的用益物权,矿业权本身是财产权、特许经营权和实际开发权的结合体,又与矿产资源国家所有权、矿区用地使用权、矿产品所有权及相邻关系人环境权等多有关联,在权利客体以及权利设立、流转、行使和消灭等方面,均具有不同于典型用益物权的特殊性。
如典型用益物权是指用益物权人对他人所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不包括处分权能;
而就矿业权尤其采矿权而言,权利的行使过程同时也包含甚至就是对矿产资源的处分过程,当许可矿区的储量开采完毕后,不仅作为用益物权的采矿权消灭,矿产资源所有权也因客体不存在而相应灭失。
值得注意的是,现行涉矿法律、法规大多制定在计划商品经济阶段或者从计划商品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阶段,行政管理色彩较浓厚,市场交易规则相对匮乏,已不能完全适应矿业权流转日益市场化的发展趋势,与国家正在推进的“放管服”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发展方向亦不完全相符。
《民法典》虽仅以一个原则性条文界定矿业权的用益物权属性,但对于凸显矿业权的物权属性,革新矿产资源立法理念,促进矿业权依法流转,具有重要意义。
2017年7月27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矿业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对矿业权出让、转让、租赁、承包、抵押等流转方式予以规制,尤其其中关于矿业权转让申请未经批准前转让合同效力的认定,即为对《民法典》本条关于矿业权用益物权属性的尊重和具体适用。
(二)取水权
取水权的概念,首次在法律层面出现是2002年《
水法》中,该法第48条第1款规定:“直接从江河、湖泊或者地下取用水资源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国家取水许可制度和水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的规定,向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申请领取取水许可证,并缴纳水资源费,取得取水权。
但是,家庭生活和零星散养、圈养畜禽饮用等少量取水的除外。”
2007年原《物权法》第123条进一步规定依法取得的取水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沿袭了原《物权法》的这一规定。
我国水权理论尚未形成成熟的、具有普遍共识的理论体系。法学领域关于水权概念的界定可以区分为单权说、双权说和多权说。
单权说为民法学界的通说,即认为水权是依法对地表水和地下水取得使用或收益的权利。包含两层含义:
第一,水权是独立于水资源所有权的一项法律制度;第二,水权是水资源非所有人依照法律的规定或合同的约定所享有的对水资源的使用或收益权。[6]双权说认为,水权包括水资源所有权和使用权,双权说可谓对水资源立法的一种解读,认为《水法》第3条关于“水资源属于国家所有。
水资源的所有权由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水塘和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修建管理的水库中的水,归各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使用”的规定,其核心内容就是水资源的所有和使用。
多权说则认为,水权是多种权利的集合,但如何对其精细划分又有不同观点。由此,关于水权,不仅理论歧见较大,而且从取水许可制度以及水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的施行实践来看,水权的内涵、外延,《水法》《民法典》规定的取水权与有关生态文明规范性或者政策性文件中所涉及的用水权(常与排污权、碳排放权、用能权并列使用)等相关水权利的区分、关联等问题,亦均有待进一步明确。此外,关于取水权的性质,学理界亦有多种观点。
本条规定将其界定为用益物权,但水资源的公共物品性、权利设立的行政特许以及权利交易的限制性等特点,决定了取水权具有不同于典型用益物权的公法属性。
(三)使用水域、滩涂从事养殖、捕捞的权利
使用水域、滩涂从事养殖、捕捞的权利,在法律层面上最早出现在1986年《
渔业法》,该法第10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根据国家对水域利用的统一安排,可以将规划用于养殖业的全民所有的水面、滩涂,确定给全民所有制单位和集体所有制单位从事养殖生产,核发养殖使用证,确认使用权。”“全民所有制单位使用的水面、滩涂,集体所有的水面、滩涂和集体所有制单位使用的全民所有的水面、滩涂,可以由集体或者个人承包,从事养殖生产。
”“水面、滩涂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
上述规定,使用了“核发养殖使用证、确认使用权”的表述。2000年修正的《渔业法》删除了这一表述,其第11条规定:“国家对水域利用进行统一规划,确定可以用于养殖业的水域和滩涂。
单位和个人使用国家规划确定用于养殖业的全民所有的水域、滩涂的,使用者应当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由本级人民政府核发养殖证,许可其使用该水域、滩涂从事养殖生产。
核发养殖证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集体所有的或者全民所有由农业集体经济组织使用的水域、滩涂,可以由个人或者集体承包,从事养殖生产。”采用了“核发养殖证,许可其使用水域、滩涂从事养殖生产”的表述。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修正案(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中指出:“水域是一种多用途的资源,水域有航行、灌溉、供水、行蓄洪、维护生态平衡等多种功能,全民所有的水域包括海域、江河、湖泊、水库等,可以许可由单位或个人用于养殖活动,但对单位或个人确认水域、滩涂的排他性使用权,涉及的问题较多,也比较复杂,宜作进一步研究,由规范有关物权的法律进行规定。”
2004年、2009年、2013年,《渔业法》经过历次修改,但上述“核发养殖证,许可其使用水域、滩涂从事养殖生产”的表述均未改变。
原《物权法》第123条采用了“依法取得的使用水域、滩涂从事养殖、捕捞的权利受法律保护”的规定,从基本法律的层面确认了养殖权、捕捞权的用益物权属性。
《民法典》沿袭了原《物权法》的这一规定。
关于使用水域、滩涂从事养殖、捕捞的权利,往往称为养殖权、捕捞权,并合称为渔业权。关于养殖权、捕捞权的性质,学理界存在不同观点:
(1)公权说,持该说的部分学者认为,渔业法属于公法,渔业权是主管机关基于渔业法作出的行政处分,应是公权;还有部分学者认为,渔业权的标的是一种公物,而公物则系供民众使用,因此,渔业权是一种经主管机关同意之公物使用权。
(2)私权说,包括单纯物权否定说、形成权说、渔场行为绝对说、渔场支配说、准物权说。其中准物权说认为,渔业权并非民法上的物权,但准用民法关于不动产物权的规定。《日本渔业法》第23条规定:“渔业权视为物权准用土地有关规定。”
(3)折中说。该说认为渔业权兼具公权和私权双重属性,就其内容来看确实属于私权,为私法物权,但仍受公共性的规范。考虑到渔业权因其取得必须基于许可制度,从而被烙上了公权性。“这种在法律上兼具公、私权的性质,可说是渔业权的特质。”
(4)区分说。该说从我国经济体制特征出发,认为不同所有制水域上的渔业权具有不同的法律性质。在公共水域上产生的渔业权是一种典型的附属物权,在非公共水域上形成的渔业权,属于民法上的用益物权。
本条规定,从基本法律的层面确认了养殖权、捕捞权的用益物权属性,不仅是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维护国家和公共利益的需要,更是实现该权利的有序流转和权利受到侵害的补偿或者赔偿机制构建的需要。
在原《物权法》制定过程中,关于是否明确规定渔业权以及渔业权与水权、海域使用权等相关权利的关系存有较大争议,相关论述详见前述海域使用权。
事实上,关于渔业权的概念、范围,其权利主体、客体、内容、流转,以及养殖权和捕捞权是否分属不同权利制度等重要问题,尚需留待理论和实践的持续发展。
适用指引
本条未创设新的权利类型,是在原《物权法》规定基础上,继续对《矿产资源法》《水法》《渔业法》等法律中已有权利类型的重申,其立法本意是确认探矿权、采矿权、取水权、养殖权、捕捞权在法律效力上的用益物权属性。
需要注意的是,探矿权、采矿权、取水权、养殖权、捕捞权作为特别用益物权,兼具民事物权和行政许可的双重属性,经济和生态双重价值,具有不同于典型用益物权的特征。
尤其在权利流转上,以往的法律法规多从行政监管角度施以限制,但因实践中权利流转相当活跃,导致纠纷易发多发。
由此,在相关纠纷案件的处理上,不仅存在《民法典》的一般性规范和《矿产资源法》《水法》《渔业法》等专门资源类法律规范的选择适用,还将涉及民商事法律规范和行政监管法律规则的协调适用,以及民事权益维护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利益衡平等诸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