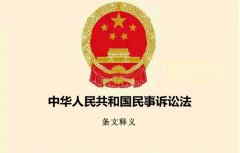2011年的“小悦悦事件”,2012年“18岁女生家门口被男友用刀砍死,保安见死不救,住户隔‘铁门’相望”等报道,引起了公众广泛热议,这一系列事件不断拷问着人们的道德良知。
近年来,公交车司机及工作人员对遭到抢劫的乘客是否负有救助义务,旅游服务机构及其导游对其带领的游客是否有救助义务,结伴旅游的“驴友”在同伴遇险时是否应当救助等社会现象和问题不断涌现,也在法律领域引起了激烈争论。
法律是否要确定人们对他人的救助义务?如何处理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如果规定救助义务,应当规定到什么程度?如何规定?
这成为《民法典》编纂过程中立法者关注的重要问题。
为了保护自然人的生命权、身体权和健康权,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自然人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受到侵害或者处于其他危难情形中时,法律应当鼓励和支持对自然人的适当救助。这种鼓励和支持体现在两个层面:
第一,对不负有法定救助义务的救助人的保护。一方面,在救助人造成受助人损害情形下,救助人责任应予以限制或者免除,对此,本法第184条予以明确规定。另一方面,救助人因救助而自己受到损害时享有请求权,对此本法第183条予以明确规定。
同时,本法关于无因管理的条文也为救助者提供了一定的保护。
第二,规定特定主体在特定情况下的积极的救助义务。本条即规定了在自然人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受到侵害或者处于其他危难情形中时,特定主体的救助义务。
关于是否规定危难救助义务的问题,存在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就目前中国的实际状况而言,一般救助义务属于道德规制的范畴,不应该上升到法律的高度。
危难救助义务法律化极易混淆法律与道德的界限,存在泛道德化危机。有学者认为,确立危难救助义务“会极大限制人们的行为自由,给个人增加不必要的负担,阻碍社会活动的开展”。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危难救助义务符合人文主义的精神,凸显法律对人的尊重和关爱以及对人的生命等重大权利的保障,体现了利益间的权衡——为了保护较为重大的利益(生命健康利益)适当限制个人自由,以免人的生命权或身体健康权遭受无法挽回的损害。
危难救助义务的设定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是具有进步性的规定。
为避免道德义务和法律义务混淆而提出过高的行为要求,本条将负有救助义务限定在法律规定的前提下。
法律对救助义务的规定,包括两种:
第一种是条文中明确规定了救助义务。例如,本法第822条、《
海商法》第174条、《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0条第1款的规定。
第二种是法律虽然没有明确规定救助义务,但规定中包含了救助义务。
例如,本法第942条第1款、第1198 条等。
(一)义务主体——负有法定救助义务的组织或者个人
本条规定的救助义务主体为负有法定救助义务的组织或者个人,但是对于哪些属于负有法定救助义务的组织或者个人,并未作出明确规定。
我们认为,本条规定的负有法定救助义务的机构或者个人主要包括以下情形:
目前,我国有关救助义务的法律规定主要有:
《
消防法》第44条第4款规定:“消防队接到火警,必须立即赶赴火灾现场,救助遇险人员,排除险情,扑灭火灾。”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0条规定了发生交通事故的车辆驾驶人对受伤人员的立即抢救义务;第72条规定了交通警察对交通事故受伤人员的先行组织抢救义务;第75条规定医疗机关对事故受伤人员的及时抢救义务。
《海商法》第38条规定:“船舶发生海上事故,危及在船人员和财产的安全时,船长应当组织船员和其他在船人员尽力施救……”第174条规定,船长在不严重危及本船和船上人员安全的前提下,有义务尽力救助海上人命。
原《合同法》第301条规定,在运输过程中,承运人对患有急病、分娩、遇险的旅客负有尽力救助的义务。
《
民用航空法》第48条规定:“民用航空器遇险时,机长有权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并指挥机组人员和航空器上其他人员采取抢救措施……”法律法规明确规定了有救助义务的情形,较好判断。
2.负有安全保障义务的
原《侵权责任法》第37条规定了住宿、餐饮、娱乐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的安全保障义务。
本法第1198条对安全保障义务作出了规定,其中第1款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机场、体育场馆、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通常情形下,安全保障义务也包括了在遭受危险时应当及时救助的义务,比如储户到银行存钱遭到歹徒抢劫受伤,银行应当采取适当措施履行紧急救助义务。
至于银行是否负有安全保障义务,如何判断其是否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中的救助义务等,则应结合具体情形进行判断。
3.其他负有法定救助义务的主体
除上述情形以外,基于特定关系也可能存在法定的救助义务,比如监护人负有保护被监护人的义务。夫妻之间是否负有法定的救助义务,基于合同关系是否产生法定救助义务等问题,均需要结合具体情况在实践中进一步探讨。
(二)应当及时施救的情形
本条规定应当及时施救的情形为自然人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受到侵害或者处于其他危难的情形。自然人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属于物质性人格权,是民事主体享有各项民事权利的前提,其价值具有不可衡量性,应当首先被保护。
为了保护自然人的首要的人格权益,赋予特定组织或者个人一定程度的作为义务。因此,本条规定的应当及时施救的情况并不包括财产权益受到侵害或者处于危难的情形。
适用指引
一、实践中需要把握与相关制度之间的关系
(一)关于与无因管理制度的区别
《民法典》总则编中的第121条是关于无因管理的规定,该条规定,没有法定的或者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而进行管理的人,有权请求受益人偿还因此支出的必要费用。
无因,指没有法定的或者约定的义务。没有法定的或者约定的义务是无因管理成立的重要条件。如果行为人负有法定的或者约定的义务进行管理,则不能构成无因管理。[5]而本条规定的义务主体是负有法定救助义务的组织或者个人。
(二)关于与《民法典》总则编规定的自愿救助行为的关系问题
《民法典》总则编中的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
该条规定的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的救助人通常为见义勇为或者乐于助人的志愿人员。而本条规定的义务主体是负有法定救助义务的组织或者个人。前者强调的救助人的主观状态为自愿,这与本条规定的救助义务有所不同。
二、本条适用的法律效果是负有法定救助义务的组织或者个人应当及时施救
首先,应当及时施救,且不得以未付费等为由拒绝或者拖延救助。
其次,施救的措施包括了亲自救助或者联系国家机关、急救机构等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