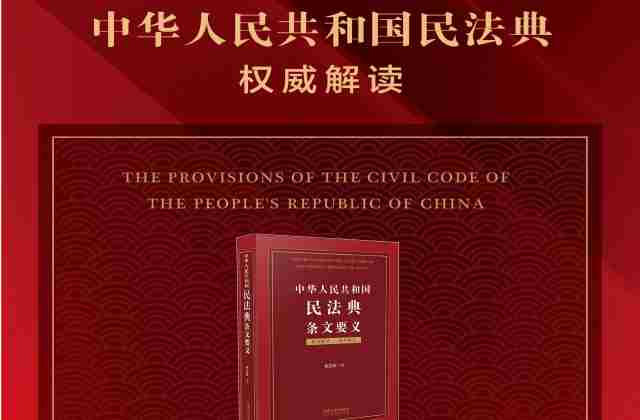依据法律规范是否赋予特定名称并给予特别规定为标准,合同可被分为典型合同和非典型合同。典型合同是指法律设有规定并赋予其特定名称的合同,而非典型合同则是指法律上尚未特别规定,亦未赋予一定名称的合同。[1]根据其构成内容的不同,非典型合同可分为以下三种[2]:
第一,纯粹的非典型合同。纯粹的非典型合同是指法律完全无规定事项为内容的合同。[3]此种合同既无特定的名称,其内容也不属于任何典型合同的事项。合同的名称和内容完全由订立合同的当事人通过协商的方式加以确定。如体育领域的运动员转会合同就是纯粹的非典型合同。
第二,混合合同。所谓混合合同,是指由数个典型(或非典型)合同的部分内容构成的合同。[4]混合合同具体表现形式可分以下四种:主从型混合合同、双重典型混合合同、类型结合型混合合同以及类型融合型混合合同。主从型混合合同。此类合同是指双方当事人所提出的给付符合典型合同,但一方还负担其他种类的从给付义务的合同。双重典型混合合同,是指合同当事人之间互负的给付义务分属于不同典型合同类型的合同。换工合同就是一种双重典型混合合同。类型结合型混合合同,是指一方当事人所负的数个给付义务属于不同的合同类型,彼此间居于等值的地位,而他方当事人仅负单一的对待给付义务,或不负任何对待给付义务。类型融合型混合合同,是指一个合同所包含的构成部分同时属于不同的合同类型的合同。[5]“半买半送”的混合赠与合同就是典型的类型融合型混合合同。
第三,准混合合同。该类合同是指在一个典型合同中规定非典型合同事项的合同,此种非典型合同一般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合同部分系典型合同,但另一部分内容系非典型合同;二是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约定了与典型合同规定相反的约定。[6]
法律之所以将经济生活中常用的合同类型予以归纳和抽象,并在法律中进行规定,赋予其名称与规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通过规定典型合同,能够简化法律适用的难度,有利于提升司法裁判的效率。在审理典型合同的案件时,可以直接依据《民法典》合同编中关于典型合同的规定予以直接适用。然而,对于非典型合同而言,由于法律缺乏直接可供适用的规则,故其法律适用难度较大,需要分类讨论。
(一)纯粹非典型合同的法律适用
纯粹非典型合同是一种最为纯粹的非典型合同,也是最能体现意思自治的合同,其名称和内容不属于任何典型合同的范畴,因此无法参照任何已有的典型合同。在适用法律时,应当明确以下两点:第一,作为一种合同,纯粹的非典型合同应当适用《民法典》总则编中民事法律行为和合同编通则的规定;第二,纯粹非典型合同内容不属于任何典型合同事项。因此,典型合同的规定在纯粹非典型合同中一般无适用的空间。
(二)混合合同的法律适用
由于混合合同的法律关系复杂,类型多样,关于其法律适用的学说,目前存在吸收主义、结合主义以及类推适用主义三种观点。
第一,吸收主义。该学说认为应当将混合合同的部分加以分解,区分其合同的主要部分和次要部分,其合同的主要部分适用相关典型合同的规定,非主要部分被主要部分吸收。此种观点在主从型混合合同中可以得到较好的适用,但其在其他类型的混合合同中难以适用。如在类型结合型混合合同和类型融合型混合合同中,很多情况下无法区分出何者为主、何者为从,存在难以探明何者应吸收何者的情形。此外,放弃合同非主要部分明显违背了当事人的意愿选择,有悖契约自由之精神,不利于当事人真实合同目的的实现。
第二,结合主义。该学说认为,应当将混合合同的各部分进行分解,并就各部分适用相关典型合同的规定,最后依据当事人可以推知的意思加以调和,进而达到法律适用统一的目的。此种学说克服了吸收主义违背了当事人意思的缺点,但其将合同整体予以分解并适用相关典型合同规定的方法,破坏了合同各部分之间的有机联系,有机械相加之嫌。
第三,类推适用主义。该学说认为,法律对混合合同既然没有明确的规定,因此,应当就混合合同各个部分类推适用相关典型合同的规定,并斟酌当事人缔约目的加以调整。类推适用的观点尊重合同当事人的意愿,保持了合同各组成部分间的有机联系,是当今理论界的通说。
(三)准混合合同的法律适用
此种非典型合同多表现为合同当事人在典型合同中就某一部分规定了非典型合同事项或对典型合同事项作出相反规定。对于此类合同,可以在其主体部分适用相关典型合同规定的基础上,判断其特别规定部分的效力,如若该部分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和公序良俗,则应当认定其有效。
民事活动纷繁复杂,合同交易类型多种多样,《民法典》只能将一些在现实生活中普遍发生并且规则较为成熟的合同类型在合同编中加以规定。合同编在第2分编典型合同中规定了19类典型合同。
其他一些单行法律也针对某一合同类型作出专门规定,例如《
保险法》专章规定了保险合同,对保险合同的定义、合同的订立、合同主体、合同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合同的履行、合同的变更与转让、合同的解除等作了较为全面、细致的规定;再如,《
旅游法》专章规定了旅游服务合同,对旅游服务合同的订立、合同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合同的解除、违约责任等作了明确的规定。
对保险合同、旅游服务合同等这些相关单行法律作出专门规定的合同,可以直接适用这些专门规定。但在经济社会生活中,大量合同类型既在合同编中没有规定,在其他相关法律中也没有明文规定,对这些非典型合同如何适用现有法律进行约束和指导,是十分重要的。
合同编通则的规定是针对所有合同的共性规定。因此,非典型合同应当适用合同编通则的规定,合同编通则对合同的订立、合同的效力、合同的履行、合同的保全、合同的变更和转让、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违约责任等所作的规定均适用于各类非典型合同。
合同编第2分编规定的典型合同,虽然是对某类合同的专门性规定,但其他一些合同可能会与合同编规定的典型合同存在共同之处或者相近之处。例如,买卖合同是典型的有偿合同,非典型合同中也有许多有偿合同,这些有偿合同可以参照适用买卖合同的有关规定。由于合同编关于买卖合同的规定对有偿类合同的指引、示范作用较强,合同编中的第646条还对此专门作了规定,即“法律对其他有偿合同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没有规定的,参照适用买卖合同的有关规定”。同样的道理,其他非典型合同也可以参照适用合同编或者其他法律最相类似合同的规定,本条对此予以明确。
本条第2款还对特定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作了规定,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履行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勘探开发自然资源合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现代合同法秉持契约自由,但立法也在特定情形下对意思自治加诸限制,以克服其过度扩张的局限性,维护契约正义的价值观念。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勘探开发自然资源合同,均属于具有涉外因素的民事合同。
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41条的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其第4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对涉外民事关系有强制性规定的,直接适用该强制性规定。”
《民法典》第467条第2款的规定就是对于涉外合同当事人法律适用选择的限制,依据该款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履行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勘探开发自然资源合同,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可以从三个方面把握此款规定。
第一,本条所规定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勘探开发自然资源合同,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履行,中国法律与上述合同具有密切联系,符合准据法的确定要素。
第二,原《合同法》第126条第2款即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履行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勘探开发自然资源合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本款沿用了之前的规则。
第三,《
民事诉讼法》第273条规定:“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履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勘探开发自然资源合同发生纠纷提起的诉讼,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管辖。”由此,《民法典》第467条第2款的规定也与程序法的规定实现了有效衔接。
适用指引
《民法典》第467条第1款规定:“本法或者其他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合同,适用本编通则的规定,并可以参照适用本编或者其他法律最相类似合同的规定。”适用本条规定时,应当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非典型合同适用合同编通则的规定。虽然法律没有对非典型合同的名称和规则进行特别的规定,但非典型合同仍属于《民法典》第464条所规定的合同。有关其订立、效力、履行、变更、解除、保全、责任承担等方面的事项应当适用合同编通则的规定。
第二,非典型合同可以参照适用典型合同或其他法律最相类似合同的规定。第三,关于参照适用对象的选择。在选择参照对象之前,裁判者应当对非典型合同中的给付、合同目的以及合同标的物等因素进行整体把握,继而在此基础之上选择合适的参照对象,以此保障法律适用的准确性与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