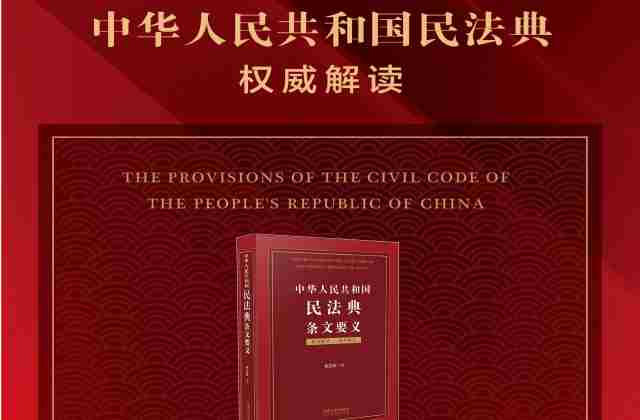从比较法的角度来看,不论是在大陆法系还是在英美法系,“要约—承诺”都被认为是订立合同的一般方式。法律或示范法的条文如《德国民法典》第145~152条、《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14~24条、《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第2.1.1~2.1.11条、《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第II.-4:201条、《欧洲合同法原则》第2:201条、《欧洲合同法典》第11~17条。我国《民法典》亦同。
“要约—承诺”方式,本质上是对当事人的合同订立过程(缔约磋商过程)进行简化和分析的模型。
在这一模型之中,一方作出的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含有所欲订立的合同的必要之点、一经对方承诺即可成立合同的意思表示,称为“要约”;一方在缔约磋商过程中所作出的完全接受要约或接受要约核心内容(未对要约内容作出“实质性变更”)的意思表示,称为“承诺”。
在一方作出可被评价为“承诺”的意思表示之前,双方在缔约磋商过程中相互作出的有关缔约的意思表示,均称为“要约”(“新要约”或“反要约”)。
通过对双方当事人在缔约磋商过程中所作出的有关缔约的意思表示进行评价(构成要约或构成承诺),可判断双方当事人是否就订立合同达成了意思表示一致,从而判断当事人是否订立了合同。
适用指引
订立合同的其他方式主要有:
一、交叉要约
交叉要约(又称交错要约),是指在当事人采用非对话方式订立合同的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向相对人发出要约,正好相对人也向其发出一份内容一致的要约。交叉要约之所以被归入“要约—承诺”以外的其他方式,是因为在“要约—承诺”方式中,被评价为承诺的意思表示的发出时间须在要约到达之后,须是受要约人了解了要约的内容后作出接受该要约的意思表示。除时间因素及因此所带来的差异外,交叉要约与普通的以“要约—承诺”方式订立合同没有区别。交叉要约的发生纯属巧合,因而其在实务中发生的概率极低。我国学者大多承认交叉要约属于订立合同的方式,承认此种情况下可以成立合同。
二、意思实现
在以“要约—承诺”方式订立合同时,当事人需要各自作出缔约的意思表示。并且,原则上,此种意思表示属于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在到达相对人时生效(以对话方式作出的,相对人知道其内容时生效,《民法典》第137条),且在承诺生效后合同才成立(《民法典》第483条)。在特殊情况下,受要约人从事了某种履行行为或受领行为,此种行为若适用有关默示意思表示的规则,仍在到达相对人时意思表示生效、合同成立,则于行为人保护有所不周。为实现对行为人的周到保护,学说承认,在例外情况下,当事人可以意思实现的方式订立合同,即受要约人从事了某种可认为其有承诺意思的行为,在受要约人从事此种行为时,合同成立,无须受要约人的承诺意思到达要约人(《民法典》第480条但书、第484条第2款)。
对于意思实现是属于“要约—承诺”方式以外的其他方式,还是属于“要约—承诺”方式中的一种特殊情形,学说上存在争议。不过,此种争议仅是对术语外延的理解不同,于具体规则适用没有影响。自文义而言,《民法典》第480条、第484条第2款将意思实现表述为不需要通知的承诺,从而对承诺采广义理解,由此,将意思实现作为“要约—承诺”方式之内的特殊形态似乎更能避免语义矛盾的质疑。
三、以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
有学者将以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归入“合同订立的其他方式”。不过,如前所述,订立合同的方式与合同的形式不同。合同书是合同的形式,是书面形式的一种类型(《民法典》第469条第2款、第490条),不属于订立合同的方式。虽然从事后的角度判断当事人是否就合同内容达成了合意、合同是否成立时,若当事人以书面形式中的合同书形式订立了合同,一般来说,再对当事人是否作出了要约、承诺进行逐一分析和判断已无必要。但是,从事中的角度进行分析,以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绝大多数情况下仍为以“要约—承诺”方式订立合同(极个别情况下以交叉要约方式订立合同的除外)。并且,若当事人虽然是以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但如果双方当事人是以各自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签署合同书的形式订立合同,那么,在特殊场合,仍需对当事人是否作出了要约或承诺、要约或承诺是否生效或被撤回等问题进行分析。
四、强制缔约
有学者将强制缔约归入“合同订立的其他方式”。但是,根据《民法典》第494条的规定,不论是在国家下达国家订货任务、指令性任务的场合,还是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当事人负有强制缔约义务的场合,当事人仍是以“要约—承诺”方式订立合同,只不过当事人的缔约自由受到了国家任务或法律、行政法规的限制而已。根据《民法典》第494条第2款和第3款规定,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负有发出要约义务的当事人,应当及时发出合理的要约;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负有作出承诺义务的当事人,不得拒绝对方合理的订立合同的要求。可见,强制订约至少在形式上并不属于“要约—承诺”以外的合同订立方式。
五、事实合同
“事实上的合同关系”(或称“事实合同”)这一概念,系由德国学者豪普特(Günter Haupt)于1941年提出。其核心观点是,当事人之间可以因为一定的事实过程而成立合同,此种合同的成立不需要当事人达成合意,但其仍具有合同内容的实质,因而只是成立方式与传统的合同不同,关于其内容仍应适用合同法的规则。关于“事实上的合同关系”,豪普特将其类型化为三种:一是基于社会接触而产生的事实上的合同关系,如当事人为缔约而进行社会接触的过程中一方对另一方负有照顾、通知、保护等义务;二是基于团体关系而产生的事实上的合同关系,主要是在合伙合同或劳动合同无效或被撤销时已形成的事实上的合伙或劳动关系;三是基于大企业经营公共事业的过程中所产生的事实上的合同关系,如供应电、水、气等法律关系。“事实上的合同关系”理论提出后,在德国法学界产生激烈争论。其中第三种类型曾被德国学者拉伦茨(Larenz)教授所认同,并将其改造为“社会典型行为”理论,又曾被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的裁判中所采纳。但后来德国联邦最高法院逐渐不再采纳这一理论进行裁判,包括拉伦茨教授在内的德国学者也大多放弃了这一理论。
我国实务界所大量使用的“事实合同”一词,究其本质而言,与德国学者豪普特所提出的事实合同完全不同。我国实务界所说的“事实合同”,绝大多数是指双方未以书面形式(特别是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而是以口头形式达成合意或以行为默示地作出缔约意思表示。之所以将这类合同称为“事实合同”,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的合同形式强制思维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制定的“三大合同法”都奉行合同形式强制原则,原《经济合同法》规定“经济合同,除即时清结者外,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原《经济合同法》第3条),原《涉外经济合同法》和《技术合同法》也都分别规定合同必须以书面形式订立(原《涉外经济合同法》第7条、原《技术合同法》第9条)。此外,1994年通过的《
劳动法》也采合同形式强制原则,规定劳动合同应当以书面形式订立(第19条)。受此影响,许多实务工作者形成了以书面形式订立的合同才是合同、未以书面形式订立的合同只能称为“事实合同”的观念。本质上,德国学者豪普特所提出的“事实合同理论”,是要适用合同法的规则去处理当事人欠缺缔约合意甚至一方当事人根本未作出意思表示(或所订立的合同未被追认、无效或被撤销)的情形。对于其所列第一种类型(基于社会接触而产生的事实上的合同关系),在我国,应当适用侵权责任规则或缔约过失制度加以处理。对于其所列第二种类型,应适用有关合同不被追认、无效或被撤销后的不当得利返还等制度加以处理,若在价值判断结论上认为适用不当得利返还等制度加以处理所得出的结论不够公平、对当事人保护不力,正确的做法应是对合同无效制度、合同撤销制度、不当得利返还制度等加以完善,而不是绕过这些制度另谋出路。对于其所列第三种类型,可适用强制缔约制度、意思表示解释制度等加以解释和处理。可见,对于豪普特的“事实合同理论”所针对的那些问题,我国民法已有相应制度能够妥善加以处理。
总之,我国实务界所习惯使用的“事实合同”一词与德国学者所讨论的“事实合同”完全不同。我国实务界所习惯使用的“事实合同”涉及的是合同的形式问题,涉及的是《民法典》第469条。德国学者曾提出的“事实合同理论”涉及的是订立合同的方式,是能否突破“要约—承诺”方式所要求的缔约合意的问题,是在欠缺缔约合意或缔约合意已被法律加以否定的场合能否适用合同法规则去处理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的问题。所谓“事实合同”不是本条所规定的当事人订立合同时在“要约—承诺”方式之外所可以采用的其他方式。[1]
六、竞争缔约
竞拍是一种特殊的要约、承诺方式,有时也被理解为是一种其他的订立合同的方式。不同于通常情况下要约、承诺当事人一对一的关系,整个过程具有动态性的特点。在拍卖中,竞买人的出价为要约,有不同的竞买人,在现场拍卖的场合,每一次新的出价,都意味着竞买人的变化,竞买人不断变化,要约人就不断变化,前者的要约不断被后者的要约刷新,价高者得,拍卖人击槌为承诺,整个缔约过程体现出一种竞争性。后要约人发出要约后,前要约人的要约即失效,拍卖人不能再对前要约人进行承诺。在招投标中,违反招投标法等竞争性缔约方式订立的合同,属于违反法律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合同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