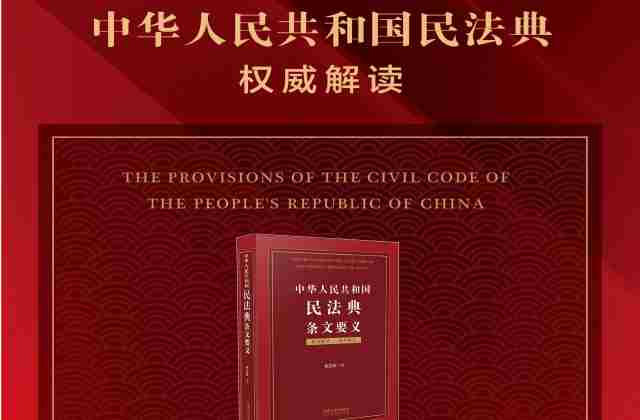保管凭证,是指由保管人出具的用于证明确实存在保管关系的单据,它表明保管人已经收到了保管物。保管凭证既是保管合同成立的一种证据,又是保管物验收凭证。保管凭证最主要的作用在于证明保管物已经交付,保管合同成立。同时,保管凭证又是当事人义务履行的依据和发生纠纷时裁判的依据。根据本条规定,寄存人向保管人交付保管物时,保管人应当同时出具保管凭证。但给付保管凭证不是合同成立的要件,也并非保管人必须履行的一项义务。如果根据交易习惯,保管人不出具保管凭证的,则按照交易习惯处理。
关于保管凭证与保管合同的关系,有的学者主张,在有保管凭证的保管中,保管人出具保管凭证后,保管合同始为成立。在无保管凭证的保管中,保管合同自寄存人交付保管物时起成立。这种观点的前提还是承认保管合同是实践合同,只是在有保管凭证的保管合同成立的时间上提出了不同的主张。这种观点没有解决在有保管凭证的保管合同中,在寄存人交付保管物后,一旦保管人应当出具而未出具保管凭证,合同是否成立的问题。所以,不能把出具保管凭证作为合同成立的形式要件,而是应以寄存人交付保管物作为合同成立的形式要件。只要寄存人交付了保管物,即使保管人应当出具保管凭证而未出具,也应当认定保管合同成立,否则极不利于保护寄存人的利益。
从原则上讲,寄存人向保管人交付保管物后,保管人就应当出具保管凭证,但当事人另有约定或者依交易习惯无需出具的除外。例如,在车站、码头等设立的小件寄存处,一般的交易习惯是出具保管凭证。而在某些商场外的停车场,按照交易习惯就不出具保管凭证,只要有车位就可以停车,只是出来时需付款,保管人出具收款凭证。
现实生活中,人们为了互相协助而发生的保管行为,多是无需出具保管凭证的,因为这是基于寄存人与保管人之间互相信任。但是,出具保管凭证在现实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中具有重要意义。保管合同为不要式合同,多数情况下只有口头形式没有书面形式,因此,保管凭证对确定保管人与寄存人、保管物的性质和数量、保管的时间和地点等具有重要作用。一旦双方发生纠纷,保管凭证将是最重要的证据。
保管凭证是否交付涉及习惯成为法源的标准,但理论界的观点不一。有学者主张,具体习惯成为法源,需要具备四个条件:时间上的持续性、范围上的普遍性、认知上的共识性、内容上的合理性。还有学者主张,民事习惯应具备以下三个要件才可以作为制定法中的民法典的法源:一是被民众自觉接受;二是不违反公序良俗;三是具有法律上的积极效果,能够引起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变动。
有学者在《民法典》编纂之前曾经提到,应该通过以下三种方式对待和处理民事习惯:第一,吸纳转化。经过具体实际的调查之后,对于已经司空见惯的习惯纳入法典。第二,法源认可。即将一些合理的习惯背后所体现的原理抽象出来,凝结成抽象法律渊源,类似公序良俗原则,放置在原则地位,对法律规则起到补充、补漏的作用。第三,适用认可。即习惯和法律规定不相同时,优先适用习惯,原《合同法》第368条便是如此。
判断习惯能否成为法律渊源有两项标准,第一项是习惯的适用不会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第二项是习惯的适用符合公序良俗原则的要求。需要注意的是,为了便于法官在司法裁判中顺利援引,我们应当对社会生活中存在的民事习惯进行深入的调查、归纳和总结,[3]这能够更好地保障合理的习惯成为法律渊源的保障。《民法典》第10条规定,习惯在法律没有规定时可以适用,这原则上明确了习惯与制定法适用的先后顺序,明确了习惯作为补充性法源的定位。
比如,本条“寄存人向保管人交付保管物的,保管人应当出具保管凭证,但是另有交易习惯的除外”,其中便规定了交易习惯优先适用的情形。即按照双方长期的交易习惯,若一方即使不出具保管凭证,另一方也会作出履行保管合同的行为,此时保管凭证的存在似乎并不是太过重要,其存在与否并不会影响保管合同的成立,不是保管合同成立的必备要件之一。
适用指引
保管凭证虽然也是保管人在收到保管物后给寄存人开具的单据,但与仓储合同中保管人收到仓储物后开给存货人的仓单不同。根据本编第22章仓储合同的规定,仓单是保管人收到仓储物后向存货人开付的提取储物的凭证。除作为已收取仓储物的凭证和提取仓储物的凭证外,仓单还可以通过背书,转让仓单项下的所有权,或者用于出质。根据本法第910条规定,存货人在仓单上背书并经保管人签订或者盖章,转让仓单发生效力。
存货人以仓单出质应当与质权人签订质押合同,在仓单上背书并经保管人签名或者盖章,将仓单交付质权人后,质押合同生效。而相对于保管合同而言,保管凭证并没有被赋予更多的含义,只是保管人交付给寄存人的凭证,法律也没有明确保管凭证是寄存人提取保管物的凭证。但对于保管人和寄存人而言,保管凭证也是保管人收到保管物、寄存人提取保管物的重要证据。